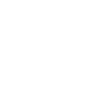最新更新日期 2018-03-29 by 張添皓醫師的牙髓診療室
幾年前,我們在台大總院的牙科醫師,是需要輪流派駐至台大雲林分院支援。與其說是支援,不如說是「外放」。
為什麼說是外放呢?對我這土生土長的北部人來說,到達雲林的交通,超級不方便。那時候,虎尾的高鐵站,還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,以及虎尾宿舍前的兩旁芒草比人還高的。鄉間小路。
兩年內,還去了兩次。最後一次支援,也是在寒冷的除夕夜前,結束最後一天的支援。
凌晨開往斗六的火車
那年過年特別冷,可能是氣候變遷的關係吧!心想著,這一次結束後,就可以回台北跟家人過年了。
週日,捨不得太早離開台北,並不是享受五光十射的台北;而是想在最後一秒前,多點時間在家吃頓晚餐、洗個碗盤、整理明天要倒的垃圾。
趁著昏暗的週一凌晨,悄悄掀開溫暖的被窩一角,棉被塞得緊緊,躡手躡腳關上房門,冰箱上貼上字條「週五晚上 8:45 到台北」。
搭上往斗六台鐵夜車,出乎意料之外的,有志一同的游子,很有默契的在這班凌晨的夜車,以鼾聲互相打招呼。
走出斗六火車站,只有昏黃的路燈眨呀眨,好像在跟我說,歡迎光臨斗六。
「匡噹!」踢到一個深咖啡色的維士比玻璃瓶,彈到旁邊那個被踩扁沾滿深紅色檳榔渣的白色衛生杯,紅色檳榔汁狠狠地飛濺到我的 Air Jordan 13代。〈心中咒罵著哪一個亂丟檳榔渣的傢伙。〉
古早味的 Uber
「肖年仔!坐車,到哪?」嚼著檳榔,穿著藍白拖鞋的阿伯,頭上新興宮三個字的黃底黑字帽子特別顯眼。
「台大雲林分院!」因為趕著去醫院上班,沒想那麼多,隨口應了一聲。
「不是虎尾那邊吧!?100元!」「呸 ~ 」一口檳榔渣吐在車邊。
「來!肖年仔,上車!」阿伯掏出口袋鑰匙打開這台鐵灰色的裕隆,把黃色帽子就甩在附駕駛座上,企圖想蓋住深咖啡色玻璃瓶的維士比。
〈心想:疑?不是黃色計程車嗎?怎麼是這輛看起來快 20 年早就應該作古的裕隆國產。〉
不妙,好像誤上古早味的Uber。說真的,不是我對野雞車有什麼歧視,只是純粹的不安全感湧上心頭。心中無數個的小劇場上演著,就怕被綁架之類的。偏偏那時候根本沒有智慧型手機,哪來的警政署 APP 的守護安全呀?
不管二月的清晨有多麼寒冷,我只好搖下車窗;對,你沒看錯,是「手動搖」下車窗。除了受不了滿車的煙味、檳榔汁的氣味外,準備萬一有什麼隨時可以對外頭喊救命。
「肖年仔,你是哪一科的先生啊?」
「牙科!」
「嘟好!せんせい〈先生 , sennsei 〉,我那顆牙齒搖的很厲害,昨天又整個給他腫起來,我可以去找你看嗎?」
「好!」
車內煙味太重,實在不想多說什麼,很怕再講個兩句話,我就暈車了,只好繼續望著窗外,祈求快快平安到達。
這一趟附了 100 元,說是誤上賊船呢?不如轉個心境,以懷舊這兩字做總結吧。
下車前,司機大哥還不忘問我:「先生,你叫什麼名字啊?我要去掛號啊 ~」
~ 待續 ~
~斗六台大,結束早診42人的轟炸,與喝著維士比加養樂多的阿伯〈下〉
延伸閱讀
凌晨一點半,澆著花、哼著夜來香的阿伯!
護理師小谷 vs 病房中18歲的小菸腔
跨年夜,牙科急診的康士坦丁
作者:張添皓 牙髓專科醫師